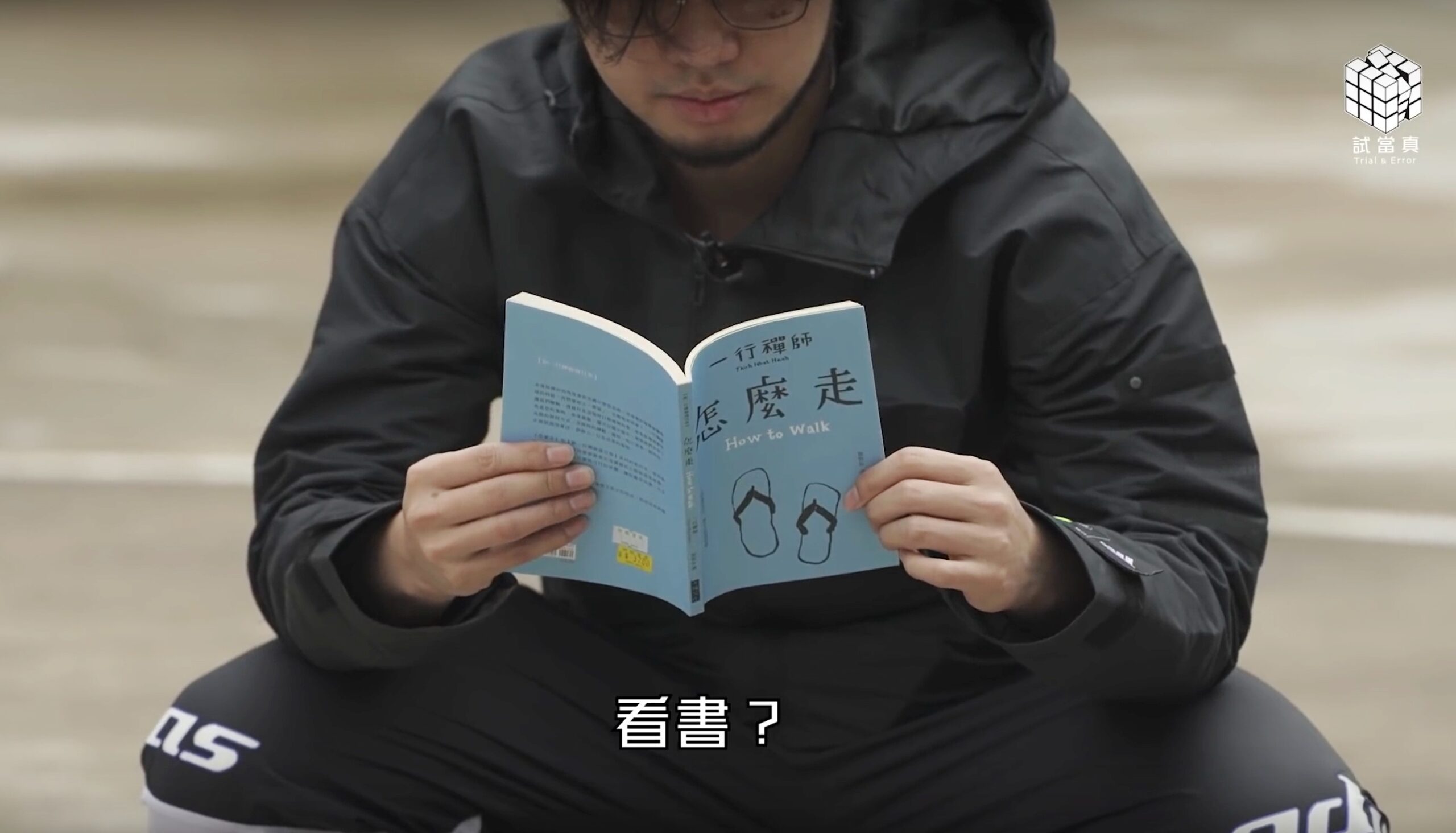附:好撚後悔冇多謝老師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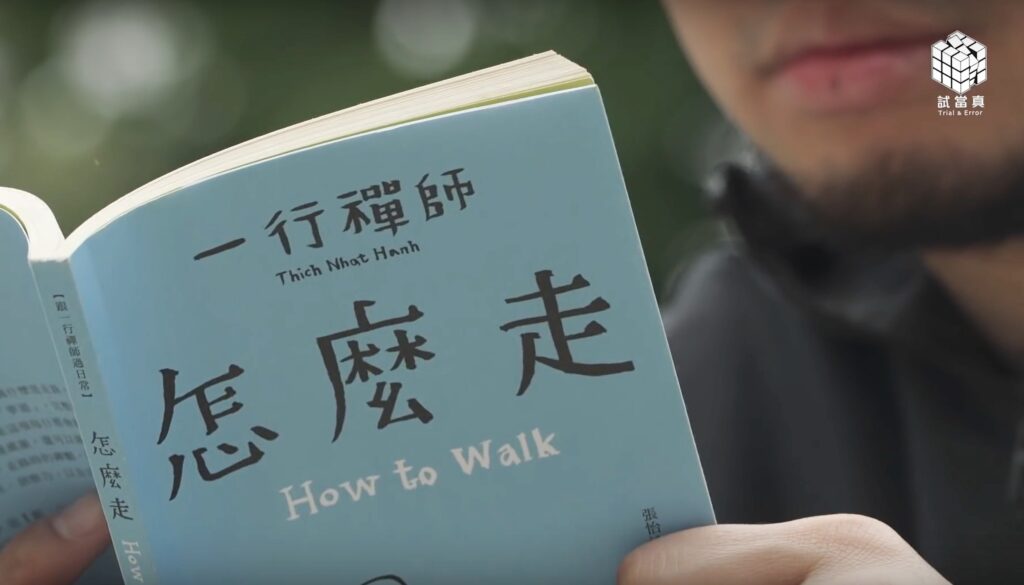
1.
英雄片的故事從來都大同小異。
已經顯姓揚名的大英雄(鋼鐵俠)遇到初出茅廬的年輕人(蜘蛛俠),踏上自己也走過(柒過)的人生路,會情不自禁心生柔情視同己出,最後不惜犧牲自己讓下一代繼續上路。但主角死而無憾,因為他通過成全對方得到救贖。
許賢沒有死,但紀錄片的結尾他終於肯丟掉留住多年的經濟科筆記,算是埋葬過去的儀式,獲得釋懷的新生命。
2.
許賢在電影裡不時在家受訪,儘管背景已成焦距外的散景,但還是可以瞥到書架上其中一本書是康納曼(Daniel Kahneman)的《雜訊》。
《紐約客》報道康納曼是夜型人,大約深夜三點才睡覺,因而錯過塞勒(Richard Thaler)朝早給他的電話。當塞勒得知自己獲諾貝爾獎,第一通電話就是打給提攜他的康納曼。兩人先後於 2002 及 2017 年獲經濟學獎。
康納曼回想兩人相識之初,塞勒仍是無名之輩,在羅徹斯特大學(University of Rochester)完成博士,那是一所優秀大學,但與所謂「頂大」還相距甚遠。塞勒的學術生涯諸多不順,備受冷待,他的論文不搞主流經濟學崇尚的數學,更要命是他批判其圭臬「理性經濟人」。
傳統經濟學強調「理性經濟人」是 as if principle,人不是百分百理性,但假設人是理性動物,依然會得到最好解釋。然而康納曼則以貓為喻,「思考對於人類就像游泳對於貓,他們可以做但不想去做。」(Thinking is to humans as swimming is to cats; they can do it but they’d prefer not to.)
若果「理性經濟人」無法準確解釋人類行為,就是時候另覓新路。康納曼與塞勒合作,結合心理學和經濟學而成為顯學,造就書店成行成市的《推力》和《快思慢想》、以及無數「認知偏誤」和「行為經濟學」的普及讀物。
往後塞勒終於出頭當上芝加哥大學教授,《紐約客》披露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大老米勒(Merton Miller)極力反對塞勒獲聘;另一諾獎得主席勒(Robert Shiller)更透露塞勒說過,米勒在大學遇到他時從不曾正眼望他。
塞勒獲獎後芝大立即舉行記招,拿到免死金牌的他一開口便是「有骨」的「暗串」:「我頗肯定這回是校長、教務長和院長第一次談到我時不會說 pain in the ass。」接著他說諾貝爾獎稍稍彌補了他拿不到奧斯卡獎的遺憾(他曾在電影《孤注一擲》客串解釋何謂「熱手謬誤」)。
3.
若果當年許賢讀到中大經濟系,他的本科生涯可能仍是由張五常主導的傳統課程,卻適值新的顯學正開始改朝換代。
若果他「成功」走上很多人爭崩頭的人生路,他可能會陷入「沉沒成本」和「確認偏誤」,不甘放棄已經付出太多的選擇,成為隨俗浮沉的打工仔,我們路過不會認得他。
回望過去,我只喜歡讀書但不擅長讀書,中學歲月沒任何事值得記住。但我始終記得一幕,忘了是中四還是中五,我正沉迷於張五常,拿住他的書見到中文科老師。
老師在中大畢業,問我在看什麼書,我秀給她看,她欲言又止但始終不置一詞,轉談其他事。當年我完全不解其意,往後多年才明白眼神背後的意思。
張五常在經濟學有何成就,我完全沒資格置喙。但他的文風害了香港整整一代人,長大後我才明白那種不斷吹噓「我識邊個邊個」的文章是多麼難看。
我不再讀張五常的書,家中唯一倖免的藏書只有《存亡之秋》,識者自能明瞭。或者換個說法,張五常成為我的反面教材。每當我受名利所誘,也有想認親認戚的時候,就要提醒自己張五常的文章是多麼嘔心,千萬不要成為那種人。
當年老師欲言又止,是不想用老師的身份指指點點,寄望我能夠自己成長自行會意。我很後悔始終找不到機會多謝她。她不但是我的老師,而且是尊重學生的朋友。
4.
最後很想告訴另一位主角,試當真沒有割席,沒有落井下石,沒有視同陌路,他們是你真正的朋友。無論將來是一沉百踩還是苦盡甘來,請記住塞勒的際遇,你一定要珍惜他們,特別是許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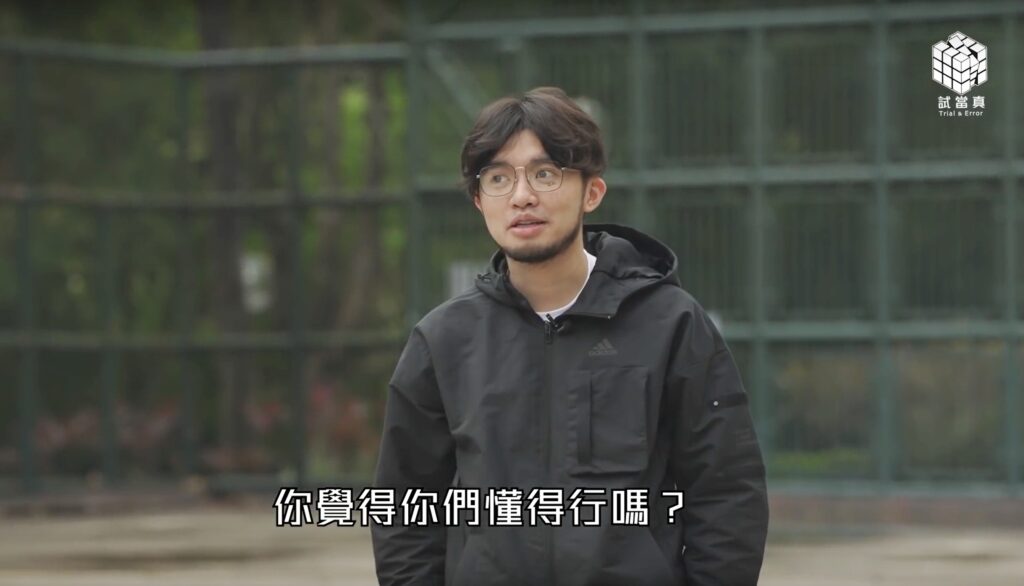
參考文獻
甄梓鈴〈《公開試當真》許賢 ╳ 梁奕豪 — 致曾被成績定義的我們〉
John Cassidy, “The Making of Richard Thaler’s Economics Nobel”, The New York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