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一位提早退休的公務員在 97 年前入職,他仍記得當年梁銘彥被迫退休,葉劉淑儀成為香港史上首名女士當上入境處「一姐」,在升降機裡見到她的情境。
資歷讓他離職前的月入不止「四皮」。我情不自禁想起自己,別說四皮,我一生從未拿過人工超過兩皮。但他放棄了本可袋袋平安直到退休的生活,原因不說自明。他主動談起蔡元貴,因為報讀再培訓課程的他也考到水喉牌,現在當輪更的接線工作,工餘前來旁聽。
興許因為工作關係,一天他早至七點來到西九龍法院,比若干「排隊黨」更早到而混在其中。讀者可想像他的樣子,天生就是一幅「公務員」的面孔,一個頂著啤酒肚且慈眉善目的中佬,比 Body Shop 的產品更加人畜無害,沒有任何刺激和副作用。在旁的青年不疑有他,肆無忌憚談到時薪多寡,中介還要抽佣。
我們笑說既然這段日子都來旁聽,何不順道報名賺點外快呢?我為此「囉囉攣」了幾日,終於鼓起勇氣找「排隊黨」裡其中一名年輕人,試探地問時薪有冇過百咁高。年輕人立即澄清梗係冇,只有七八十蚊一個鐘,時薪與朋友所聞相符。
儘管「排隊黨」有「梯隊」輪更,但始終沒有專心工作,旁聽時多在睡覺、打機、睇片、還試過一次剪指甲。在他們的「微信」對話裡隱約瞥到自己名字後,我再也見不到那個坦白的年輕人。
休庭時一名司法機構的職員與朋友大談其人生觀:「邊個當家作主都冇所謂,最緊要出糧。」我認識的退休公務員正在附近。

2.
一天一對陌生的父子現身法庭,一眼就能看出這對父子來自內地,但同樣可以一眼看出這對父子沒有「任務」。兩人散發出文質彬彬的氣息,不是奉命行事的人偽裝得到。
開審前父親絮絮向兒子解釋香港法庭的運作,休庭後冒昧攀談,父親認真地問這場審訊為何沒陪審團,不諳普通話的我一度語塞。父子坦誠他倆不熟悉案情,但知道其中一名被告是梁國雄。兩人也不太聽懂英文與廣東話夾雜的審訊,但事後會看《法庭線》補足,我順道推薦《獨媒》、《庭刊》和《明報》。
孩子在厚厚的眼鏡下有著清澈的雙瞳,審訊時一直望向犯人欄搜索梁國雄的面孔。我不懂怎樣用普通話解釋繫獄的梁國雄不再是「長毛」而成了「短毛」。終審法院已裁定囚犯可留長髮是一回事;但政治現實怎樣操作是另一回事。
在庭外我還告訴父子現在作供的何桂藍在清華畢業,兩人的表情都錯愕不已。父親開口還想再問,我立即知道他想問什麼,我說不是台灣清華,是北京清華。父親的神情更加驚訝,也更加凝重,也許他想起 1989 年。
臨別前眼尖的我問兩父子揹著什麼書。父親從背包裡掏出海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,孩子從背包裡拿出一本更厚的《聯邦論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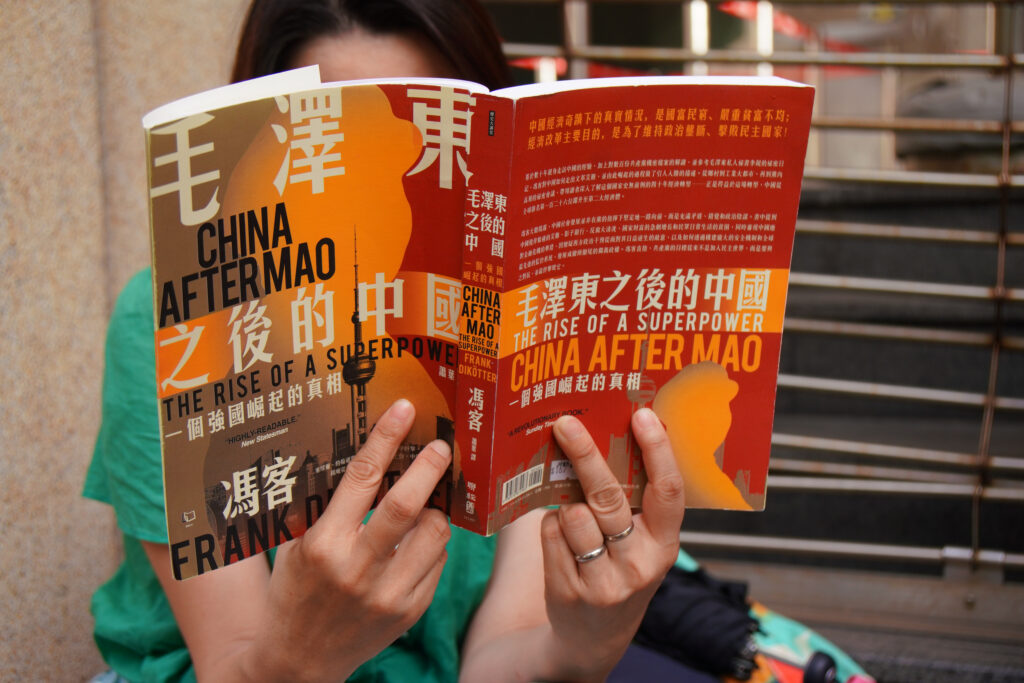
3.
我一直見證一位男生是特地去「追」鄒幸彤,他會在課餘旁聽支聯會案和初選案審訊,還告訴我將來想讀法律。我問是城大、中大抑或港大,他答港大,我的表情立即變成「睥樣」的 emoji。他看出言外之音,「我肯溫書就得。」
在何桂藍作供時,也有另一名年紀相若的男生旁聽,但他不是為「追」何桂藍而來。數日後他便要出國讀法律,臨行前特地去不同法庭觀摩各類審訊。香港人很喜歡他所讀的大學,由補習社、游泳班甚至安老院都會挪用其名字,但他自謙考不到做醫生的成績而已。
男生一直猶豫將來當事務律師還是大律師;考取外國還是香港執照。我體察到他思慮背後的深意,他知道有些案件拿了外國執照便未必能夠參與。穩重的他正尋找平衡之道,既能夠保障生活,也夠承擔義務。
男生先往高等法院旁聽一宗綁架案(HCCC2/2019),聽到控方向陪審團講解他們的角色是 Judge / Trier of fact;而法官的角色則是 Judge / Trier of law。他很欣賞律政司代表的陳詞,那就是他熟悉的普通法。然而去到西九龍法院旁聽沒有陪審團的初選案,他覺得法官兼任了兩個角色。
我問他為何想讀法律,他說「喺唔公平嘅地方長大,你會想起身為自己辯護。」後來他反問我旁聽時有否感到無奈,我答初時會有一點,但後來卻感到希望。不在有罪或無罪,而在歷史的曙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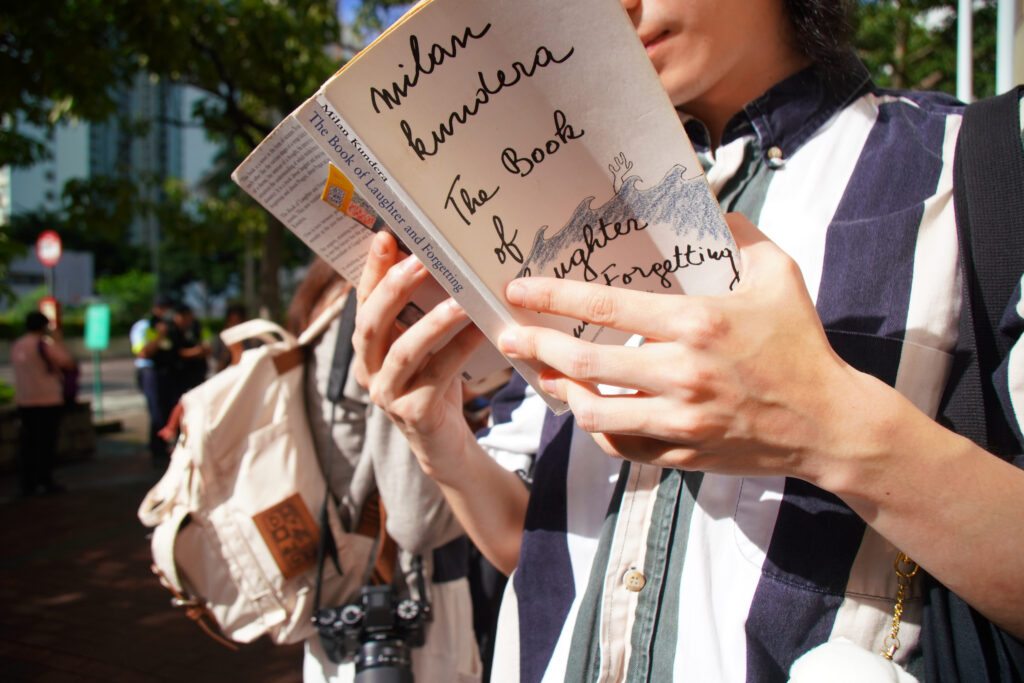
4.
我不敢向高才生分享我正在讀《蘇格拉底哲學特快車》,我只有本事看二手哲學詮釋,還要是中譯本。但我很喜歡作者訪問了雅各・尼德曼(Jacob Needleman),憶述他讀哲學的緣由。
雅各在 11 歲的時候認識亞拉斯(Elias)。他們無所不談地討論哲學,彼此互視為最好的朋友。後來雅各首次聽說「白血病」這個詞語,兩人見面的機會愈來愈少。
他倆最後一次討論的問題就是「人睡著後去了哪裡?」一天雅各因打棒球而晚了回家,母親異樣地對孩子說 I’m sorry about Elias。雅各霎時不明所以,頃刻恍然大悟,他一邊啕哭一邊跑往亞拉斯的家。
亞拉斯活不到 14 歲便永遠睡去,給雅各留下最大的疑問:為何是他而不是他?雅各自忖受到召喚去解答這個問題,鑽研哲學成為教授。不過望子成龍的母親始終「懷恨在心」,當別人介紹兒子是 Dr. Needleman 的時候,母親會特意「提醒」大家他只是哲學博士,不是真正有用的醫生。
雅各得到的答案就是「人類需要意義」。表面上亞拉斯受制於命運,但他不到 14 年的生命改變了朋友一生。生命如流星但意義如恆星,兩人在宇宙都恍若微塵,但受彼此的引力牽引,累積的緣份改變了更多人,往後的意義會燦若星辰。
我從男生的話裡體察到他的心聲,就算考到做醫生的成績,他也不會去做「有用」的醫生。他感受到時代的召喚,終有一天他會回來,我們都會回來,站起來為所有受苦的人辯護。
我不知道那一日何時來到,甚至不知道是否有生之年,但我已經感受得到。就像雅各明知已錯過朋友最後一面,依然要哭著去試,因為那一晚有永恆的意義,意義就是打破宿命的鑰匙。所有別離乃至生死都不足懼,最重要是有人願意為你活下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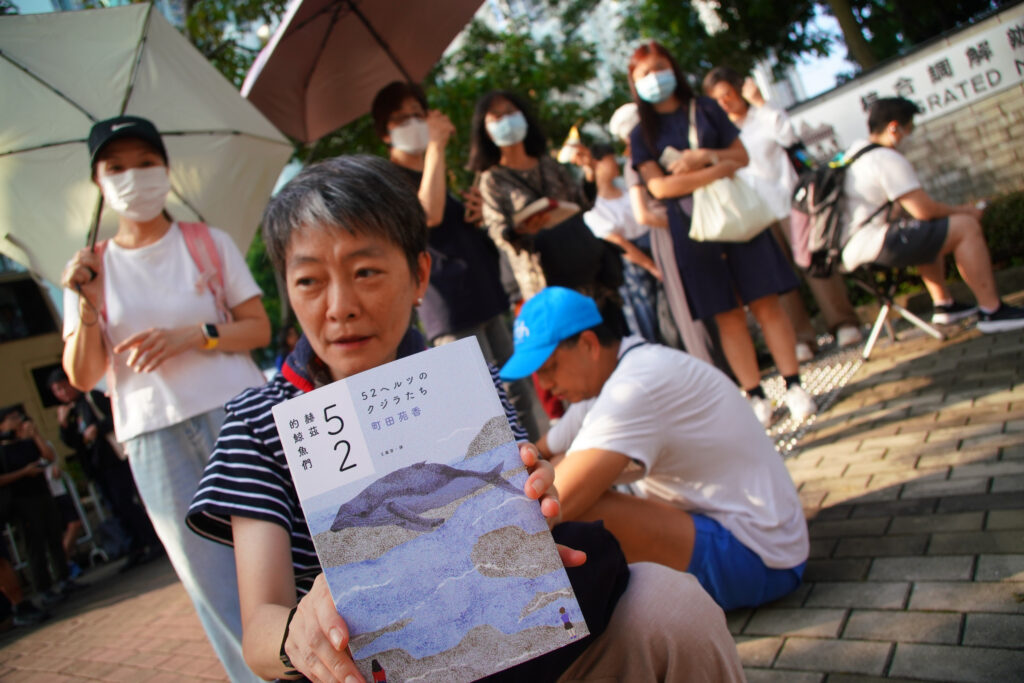
附記
拙文最初發表在 Facebook,原版刪去了第三部分其中一段,因為擔心當時寫出來會為男生帶來壓力。如今 DSE 早已放榜,男生也即將在港大法律系開始新學年,所以在此將拙文還原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