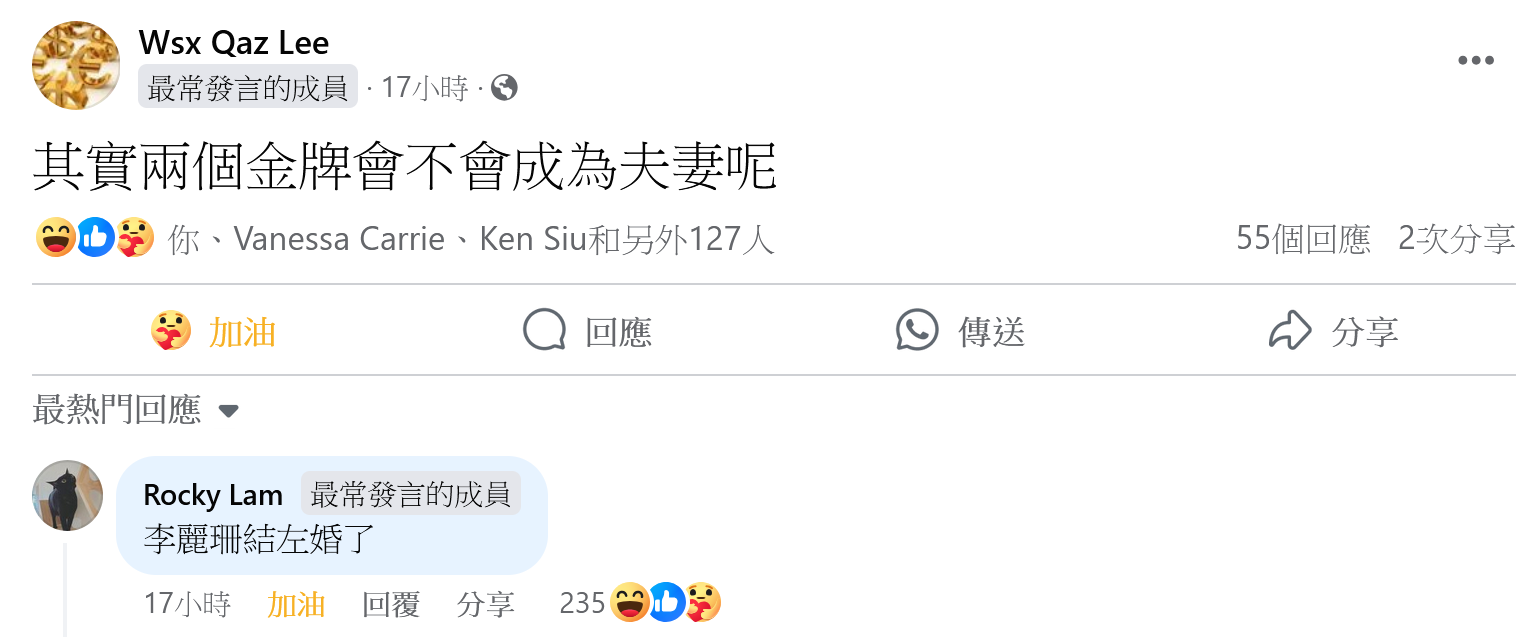1.
因為江旻憓而起的爭拗,簡直可載入捷思(Heuristic)的教科書。
人性在解釋自己過失時會傾向歸咎外部因素;但是在解釋別人過失時則傾向歸咎個人因素。若果是好事的話就相反,是為基本歸因謬誤(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)。
同樣的思維可以推而廣之適用於群體,形成內/外團體偏見(In & Out Group Bias),也叫終極歸因謬誤(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)。
如果你接受江旻憓是「自己人」,你會詮釋她的言行乃情非得已(外部因素);如果你否認江旻憓是「自己人」,你會詮釋她的言行屬高分低能(個人因素)。
對立的詮釋背後有更加深刻的疑問:究竟怎樣才算「自己人」?
2.
「我們反對在香港推行全民投票式的民主政治。。。從民主政治發展史看,一人一票制度,已經落伍失效,我們斷無理由要走回頭路的。」
上面的話是林行止寫於 1984 年的《信報》。
3.
「我們有一個斬釘截鐵的志願:決不會對不起明報的老讀者。如果環境變遷、條件變動,明報不可能再維持自由客觀的風格,我們立即關門收檔。」
「萬一 X X X X X X X,香港人失卻自由與法治,明報怎樣?明報當然停刊不出,我們辦報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,走不掉就沉默偷生,活一天算一天。在此以前,我們出版一天,就一天為維護香港人的自由與法治而努力。」
上面的話是查良鏞寫於 1983 年的《明報》。
4.
是不是和大家認識的林行止和查良鏞有點不同?根據一位曾與金庸共事的前輩現身說法,早年金庸的言論比較耿直,但隨著他多番獲領導人接見,備受禮遇,極盡尊榮,金庸漸漸和體制合作。
5.
江旻憓奪金後有人抬轎,有人指罵,但對立背後有更加複雜的合縱連橫。無論「江派」還是「倒江派」,兩邊都有異鄉人,也有留港者,既有本土派,亦有進步派,撈到亂晒。
一方面江旻憓為香港爭光;另一方面她很樂意為體制服務。其實同類的事已非第一次,究竟他/她是不是「自己人」的張力令支持民主的香港人陷入糾結。
6.
個人的觀察非常粗疏而難以作準,似乎海外港人比較嚴守「大義名分」;至於留守港人比較傾向「同理包容」。
海外港人是「活在」2019 年的香港,並且期盼長此下去;但留守港人是「活在」2024 年的香港,已隨時勢調節願景。
由於海外港人擔憂與故鄉的羈絆隨歲月消散,因此較為敵我分明,延續過去黃藍不兩立的世界觀,希望香港人一如既往保持強勢的身份認同。
至於留守港人則礙於現實的壓力而長期蟄伏,因此趨向疑中留情,寧願從低做起爭取最大公因數,希望香港人的社群在失血之際仍得以存續。
7.
我們去到舊金山或者溫哥華,都會驚訝一些華人社區就像時光倒流,回到幾十年前的「老上海」或「老香港」。因為 49 年、89 年和 97 年而移民的華人,他們對故鄉的記憶和認同都「凝結」在離去前的時代。
作為留守港人,我每見海外港人的言論,都有一種見到 Ex 的感受(雖然我沒有)。無論科技怎樣發達,都無法彌合生活在不同國度的「時差」,不只是物理上的時差,還有因政局而衍生的「時差」。只要時局不變,雙方的「時差」只會愈來愈遠。
海外港人需要注意對香港的理解恐怕「停留在過去」;留守港人則要小心對香港的理解可能「忘記了過去」。
8.
「江派」與「倒江派」除了有地理上的差異,更加微妙在政治上撈埋一碟。有些本土派選擇捐棄前嫌;有些進步派反而堅拒讓步。
米高‧瓦哲(Michael Walzer)援用俱樂部(Club)來理解共同體,你必須符合某些條件才能加入俱樂部,所以民族主義對於成員資格必然有忠誠上的要求。
至於進步陣營則崇尚《讓我們酒在一起》(The Old Oak),男主角提倡 “you eat together, you stick together.”。但就算我是最大愛包容的左膠,也不會和何君堯 eat together。
唯有團結(stick together)才能抵擋體制的不公、排外的憂患。可是瓦哲的論証對於所有政治光譜同樣有效,左膠也不會無條件地接納任何人為「自己人」,即使是進步的團結依然有道德上的要求。
因為權利和義務從來是一體兩面,必須有人願意承擔義務,其他人才可以享受權利。唯有共同的價值足以讓大家彼此承認,我們才能夠分擔義務,共享權利,避免寬容悖論(Paradox of Tolerance)。
9.
進步陣營傾向認為上述價值就是普世價值。不過很多香港人和美國人都認同普世價值,但香港人不會在乎美國隊的勝負,反而更加「肉緊」日本隊(咳咳)。
《讓我們酒在一起》的男主角能夠尊重難民,除了因為他品格高尚,更重要是他和女主角都承受失去摰愛的創傷,因而消弭同理差距(Empathy Gap),接受難民也是「自己人」。
普世價值只是構成「共同體」的必要條件,遠非充分條件。共同體的建立還需要歷史,故事裡有我們參與的位置,從而和逝者、生者、還有後代構成連結(partnership)。
10.
1996 年 7 月 29 日,李麗珊拿到香港史上首面奧運金牌。林行止連續兩日(7.30、7.31)在《信報》恭賀並討論李麗珊奪金。接著 8.1 林行止便寫下〈語重心長理不彰 民主自由莫混帳〉批評查良鏞。
當年查良鏞在書展的演講為九七後的體制護航。他說若報館老闆阻止記者發表文章,無關新聞自由,只屬「勞資分歧」;又謂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「不是一人一票普選選出」。
林行止形容「查氏這番詮釋,顯示他難逃『屁股坐在那裡』便發表什麼意見的窠臼,期待他站在港人立場發言,已屬不設實際。」
林文隨之澄清英美普選如何運作,「長期讀者知道,我們並非熱衷支持在香港實行速成式的一人一票普選;這種看法,於今未變。。。但不少香港商界精英 —— 經濟既得利益階層 —— 毫不猶豫地認同北京路綫,我們以為是大可不必的。」
有趣在林行止援引的「理據」來自他讀過喬姆斯基的書,後者當然狠批美帝的民主袒護資本主義,但對林行止而言卻是可喜可賀,「民主根本不礙事!」最後他規勸精英「沒有必要遺棄所學、昧著良知,為了附和北京而成為反民主的急先鋒。」
隨後《信報》刊登查良鏞的回信,字裡行間顯見相當不滿,「此篇『莫混帳』之社評,則實在『混帳』太甚,令人扼腕太息。」
查良鏞辯稱當日他只是說英美首長並非「直選」產生,「不加查核而率爾立論。。。似與先生平素高尚品質有間。」
今人對林行止和查良鏞的不同印象便是由此而來。2018 年查良鏞去世,林行止接連寫了三篇悼文回顧他與查的交誼,詳述兩人互有「心病」的種種因由,前述文章正是原因之一。「查良鏞先生的政治理念和手腕,則非筆者所敢苟同!」
11.
查良鏞和林行止都是香港人,兩人的生平毋庸贅言,沒有香港他們斷無今日成就。
林行止同樣備受領導人看重,據聞朱鎔基也是《信報》的長年讀者。無數名士始於當體制的座上賓,漸漸便會樂於當體制的代言人 —— 但林行止沒有。
其實林行止和查良鏞都曾明言批評普選。然而學無常師才能轉益多師,林行止的立場沒有囿於年歲而蔽於一偏,反而隨著閱歷而更加進步。
我們都參與了「香港故事」的不同角色,呈現了「香港精神」的不同面貌,但總有更好的人值得學習。在查良鏞和林行止之間,請以林行止為榜樣;在江旻憓和李慧詩之間,請以李慧詩為楷模。
12.
人生的經驗在在告訴我們,高高在上的指指點點和冷嘲熱諷都無法改變人,反而會觸發確認偏誤(Confirmation Bias)甚至逆火效應(Backfire Effect),令對方朝相反方向抱團。
我們和古代人沒多大分別,也許古代人相信怪力亂神令世界運轉,但絕太多數現代人也不清楚電腦怎樣運轉。我們只是相信科學,因為我們所屬的團體(老師、專家、信任的友儕)都這樣認為。
人是政治動物,我們有賴群體的協作才能生存繁衍,人願意為共同體而死,背後有演化上的淵源。所以人性會優先保護所屬的團體及其信念,合理化已經習慣的世界觀(System Justification)。
13.
《我推的孩子》充滿發人深省的情節,最多人討論炎上風波(第 5 – 7 集)。接拍真人騷的男主角發現節目的問題不在於假,而在於追求逼真效果。
在公眾面前呈現真實的自我,一旦與多數人相左便會受傷。反而收藏真實的自己,活在主流期待的「人設」之下,能夠保障自己在所屬的團體受到歡迎。不過代價就是像男主角般充滿壓力,而且「人設」會漸漸同化真我,當你戴慣了面具就不想脫下來。
對於很多人來說,被排擠的「社會性死亡」比真正的死亡更可怕。若果我們還有善意想改變對方,理據是重要的,但更重要是讓對方有出走的動機,有成為「自己人」的機會。
14.
我沒有在爭拗站邊,因為歷史告訴我已非第一次;還有歷史提醒我捧得一個人太高適足以害之;而且歷史安慰我即使有天之驕子為體制所用,人民也不會盲目崇拜偶像,依然擁有常識,守護尊嚴。
林行止的文集特別收錄了當年讀者投書《信報》聲援他,「是我十多年所讀到最精彩的文章之一。。。大快人心!」
只要人未死故事就未完。沒有所謂時間能夠改變一切,我們唯一能夠改變的只有自己而已。
15.
最後一定要感謝張家朗。

參考文獻
葉浩《政治時差.時差政治: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》
雨果‧梅西耶《為什麼這麼荒謬還有人信?揭開你我選擇相信與拒絕相信的心理學》